戏里乾坤大 台上日月长
——记汉调桄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陶和清
2024年05月31日 汉风古韵
文章字数:1856
文章浏览数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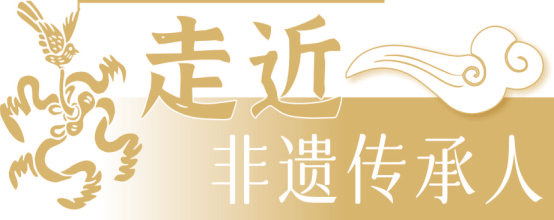
陶泓如
我的爷爷陶和清是汉调桄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,1940年出生在南郑区协税镇。这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气息和文化传承的古镇,商铺林立,商人们为了生意红火,常常自发组织社火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吸引群众、提升人气,故而民俗文化远近闻名。爷爷就是看着社火表演长大的。
由于缺少劳力,家庭生活困难,爷爷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。老话说得好: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。住在协税的汉调桄桄“同乐社”的箱主找到爷爷问:“我们的戏箱、演员都被政府接管了,改为‘南郑县新民剧社’,在铺镇成立了,现在正收学员,你娃子去不去?”在他的介绍下,爷爷走进了南郑县新民剧社。临行时没有文化的母亲含着泪花叮咛说:“孩子,你去了好好学戏,听老师的话,别做坏事,行行出状元,干工作往人前走。”告别母亲,“同乐社”背衣箱的二老爷领着脚穿草鞋的爷爷步行50多里到了铺镇新民剧社。这时爷爷年仅十岁。那时剧社是自己养活自己,生活困难不说,演出条件也很艰苦,一日三场戏,夜间没有电灯,也没有汽灯,晚上演戏,台口挂两个大碗做的清油灯。老师演主角,学员们跑龙套。由于大家都穿草鞋,群众给剧社送了个雅号“草鞋班子”。学了两年,爷爷便在老师的带领下登台演戏了。当时剧社没有女演员,主要靠男扮女装,由于他长相俊俏,嗓音清亮,被排在旦角行列,心里虽不高兴,但也不敢反对,只好服从老师的安排。
爷爷男扮女装的开门戏是《柜中缘》。11岁的他饰演徐翠莲演飞身坐到柜子上的动作戏时,个子小上不去,管场的老师就将他抱上去,但他以优美的唱腔和扮相赢得了观众的好评。第二本戏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他饰演祝英台,深受群众欢迎,轰动了城乡,《汉中日报》为此进行了专题报道。15岁时,爷爷的嗓音发生变化,由台柱子垮下来。俗话说“唱戏凭腔,卖面凭汤”,变声期的打击让爷爷对未来深感迷茫,后在老师的点拨下改习文武小生。不到两年,他掌握了高空跟头、小翻、空中扭提翻等多项技巧,开创了剧团的武戏新局面。转眼到了18岁,爷爷嗓音变得有了宽度、厚度,这正是演员的黄金时期,主要生角都落在了爷爷身上,《挡马》里饰焦光普,《三岔口》饰任堂惠,《拉郎配》饰李玉,《秀才外传》饰秀才,《山神庙》饰林冲,《武松打店》饰武松,等等。这些剧目久演不衰,深受老百姓好评。
1961年剧团迁址周家坪,易名南郑县桄桄剧团。1988年爷爷任剧团副团长主持全盘工作。1997年任剧团团长。当时面对电影电视的普及,舞台艺术受到市场严峻挑战,剧团发展每况愈下,演出市场不断缩小,爷爷为了稳定人心,守住舞台,提出了要用职业操守、人品修养、社会担当为准则,要用敬业留住观众,用改革创新适应时代、吸引观众。
2000年爷爷退休了。然而他是退而不休,一直关心着剧团的发展,关注着汉调桄桄这个古老剧种的抢救保护。也就是在同年,我出生了。幼时记忆里爷爷已经是须发皆白了,而且家中一直有一张属于爷爷的专用桌子,供他伏案绘制桄桄戏的脸谱。我常常趴在桌角看爷爷绘画,到现在还记得爷爷对我说:“这每一张脸谱,都代表着一个历史人物,不同于其他任何戏剧的化妆造型艺术。”当时我只觉得五颜六色十分生动,现在从事了汉调桄桄表演艺术,才知道,爷爷是怕这份独有的艺术失传,努力地把这些留给我们后辈。
2013年剧团招收了一批12至14岁的少年,作为汉调桄桄的后备军。在我决心要学习汉调桄桄时,爷爷对我说:“戏曲演员可不容易哦,首先要面对繁重的训练与排练。戏曲是一种技术含量极高的表演艺术,演员需要掌握大量的动作、唱腔和表演技巧,必须进行长期的训练和多次的排练。这些过程往往十分繁重且漫长,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要学就必须好好学,学出个样子来。”这也算是给我打了预防针,每当觉得练功很苦、很累的时候,我就想起爷爷的话,咬咬牙,坚持!作为传承人,爷爷给我们这些孩子排练的时候,一招一式,一丝不苟。榜样的力量大如山,在他的指导下,我们攻克一个个技巧难关、娴熟了一句句唱腔,慢慢地成长起来,成为了南郑区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心的主力军。
近年来,在剧目的编排演出中,爷爷依然承担着导演和道具制作。在“名师传戏”工程推动期间,带领青年演员导排传统折子戏《挡马》《穆柯寨》《山神庙》《武松打店》《刘胡兰》等。在老剧本老唱段的基础上,加入一些新的表演元素,排出本戏《福寿图》。在传统戏程式化的基础上不断摸索、创新,编排出现代戏《汉山魂》。他说过,剧团要发展,要排新戏,必须培养新人登上舞台,不断鼓励新人创造新的表演方式,与时俱进实现自我突破与创新。
“择一事,终一生。”爷爷非常热爱汉调桄桄,选择用一生去坚守,去奋斗,去传承。
